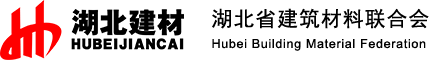結構調整的進退節奏取決于創新進程。如果制度、產業和技術創新的進展快,那么傳統和落后產業退出、收縮甚至淘汰的節奏也快。目前在中國,過剩的是產能,稀缺的是創新,創新活力直接決定了結構轉型的進程。
以頂層設計為特征的體制創新,應置于優先于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的地位。令人遺憾的是,現在不乏散點狀的技術創新,但制度和產業創新仍匱乏,這決定了調結構是艱巨漫長的過程,并非調整了有色、鋼鐵、船舶、煤炭、水泥、鐵合金的產能,新興產業就會自動雨后春筍般涌現。
投資仍是主角,硬的和軟的基礎設施投資在中國仍極其重要。中國是一個公共政策尚待完善,公共產品和服務覆蓋不均的大國。交通、物流、信息、生態、教育、醫療、養老、藝術等公共品的投資仍有很大余地。人們對環境、社會保障和教育的抱怨是明顯的證據。從硬的投資來說,信息骨干網絡、陸海空聯動的交通樞紐和骨干網絡建設仍然不足;從軟的來說,在很大程度上,城鎮化甚至就是公民權利的均等化,是市民和農民應當享有同樣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“人”的城鎮化。如果投資是政府在履行公共財政的義務,而不是越位代行企業家的膨脹沖動的話,投資仍將在未來扮演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角。
消費著眼長遠,最宜順其自然。消費往往得到過多贊美。儲蓄、節儉和克制是人類永恒的美德。負債、奢靡和放縱總會讓人類迷失。因此消費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什么角色,應順其自然,畢竟消費基本上是私人部門的行為,政府消費不是主角。人活著有多幸福,可能更多地體現在活得長久、健康、和諧和品味等質量上,而不是吃穿住行所耗用的金錢數量上。反之,過度強調消費,則往往是一些民主國家的國民逐漸懶惰,最終要么走向債務危機要么走向社會動蕩的根源。
鐘偉: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